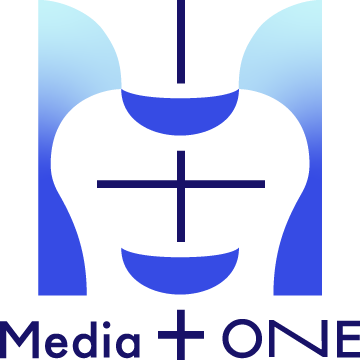中國共產黨預計於本週一(10月20日)起,在北京展開為期四天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,核心議程之一便是審議第十五個「五年規劃」。這項規劃將擘劃2026年至2030年間的中國經濟發展願景,被外界視為研判中國未來經濟路徑的重要指標。
Media+ONE特派員針對此規劃採訪多位學者及分析師,深度探討其究竟是中央政府的經濟藍圖,亦或是具備政治目的的工具。同時,報導也將聚焦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如何藉由這份「規劃」,佈局其所謂的「安全大格局」,以應對當前內外挑戰。
值得關注的是,外界同時緊盯這次四中全會可能帶來的人事異動。原先預期將在會議期間處理的高層處分案,已在會議前夕的10月17日先行揭曉,包括何衛東、苗華等九名解放軍高層,因嚴重違紀違法而遭到開除黨籍與軍籍的懲處。
根據中共黨章規範,每屆中央委員會在其五年任期內,通常會召開約七次全體會議,且每年至少一次。依照過往慣例,「五年規劃」多半在第五次全體會議(五中全會)中審議,並於隔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公佈。
然而,此次「五年規劃」卻罕見地提早至四中全會審議,外界揣測此舉可能與中國當前嚴峻的經濟情勢息息相關。分析認為,北京當局恐已無法等到明年才提出振興經濟的對策。
歐洲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所(MERICS)分析師亞歷山大·戴維向Media+ONE特派員指出,這次非比尋常的提前審議,原因在於先前第三次全體會議(三中全會)曾無故延宕,進而打亂了中共中央全會的既定週期。
回溯過往逾四十年的慣例,本屆三中全會原應在黨代會隔年,即2023年秋季召開,卻延遲近一年,直到去(2023)年7月才舉行。由於「十四五」規劃將於今(2024)年屆滿,因此新的規劃已無法等到2026年的五中全會再進行審議。
實際上,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早在2023年底便已啟動「十五五」的前期研究。今(2024)年7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在10月四中全會期間同步研究「十五五」規劃。根據政治局文件內容,中國「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,策略機會與風險挑戰並存,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。」
到了9月底,中央政治局發布會議提要,除了確認四中全會的會期,更揭示了「十五五」時期的六個「堅持」,其中針對「堅持黨的全面領導」一項,特別強調必須貫穿「各方面全過程」,並提出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」的指導方針。
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向Media+ONE特派員分析指出,「十五五」規劃的指導核心,在於以國家的「安全大格局」來主導「發展大格局」,這明顯帶有強烈的「政治掛帥」色彩。
夏明教授認為,在「黨領導一切」的指導思想下,經濟被視為服務於黨的最高利益與目標的輔助工具。當前中國經濟表現不佳,已對習近平構成政治危機,因此他預期此次規劃將充斥濃厚的政治意圖,也是對這場危機的回應。
夏明教授進一步指出,自習近平於2012年接任中共總書記、隔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,經濟政策曾由不同派系的李克強主導,當時較偏重市場導向。然而,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強與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何立峰皆為習近平的親信,上任至今已過半任期,對各部門運作瞭若指掌。因此,他將「十五五」形容為習近平執政團隊「全面主掌中國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規劃」,預估將採混合經濟模式,將私人企業整合至國營體系,強化國家的掌控力道。
2021年,適逢中共建黨百年之際,習近平宣布中國已全面實現小康社會。隨後,中共便強調將藉由「十四五」、「十五五」及「十六五」這三個五年規劃,逐步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,其中「十五五」被視為承先啟後的關鍵時期。
夏明教授闡述,此一關鍵性在於習近平目前已進入第三個任期,2027年將是一個重要節點。屆時中共將召開第二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,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百週年。他分析,若屆時無論是在國家統一或經濟小康兩方面都無法交出亮眼成績單,習近平顯然在2027年將難以順利進入其第四個任期。
夏明教授推斷,習近平對此情勢感到焦慮,加之地緣政治的不安全感日益加劇。習近平過去已將各項議題「安全化」,他認為國家安全同樣奠基於經濟安全之上。因此,「十五五」規劃中的戰略支柱產業,預估將聚焦於國防工業、航太及半導體等軍工或高科技領域。此舉在全球層面恐將加劇軍備競賽,升高周邊國家不安感,導致區域情勢不穩,但同時也能鞏固習近平的國際戰略形象與其個人安全,並透過這些發展來「震懾中國民眾」。
另一方面,熟悉中國事務的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持不同觀點。他認為,「五年規劃」雖然隱含著中共權力的展現,並能一窺決策者的權力分配,但其核心重點依然是經濟擘劃。他進一步指出,在中美摩擦日趨劇烈的背景下,外界更加關注中國與全球在經濟議題上的衝突,「五年規劃」的重要性也因此日益提升,「因為無論是中國高層還是民間百姓,對於經濟及民生問題的關切度都遠高於政治。」
不過,劉銳紹亦強調,習近平的權力基礎依然穩固,目前並未出現重大的政治爭議。他判斷「十五五規劃」的重心仍在經濟面向,即使中國國內面臨嚴峻的經濟困境,民間怨聲載道,但尚無明確跡象顯示已達爆發臨界點。因此,他認為「政權不會因此垮台」,因為政府會動用行政甚至專制手段來推動政策,並壓制異議聲浪。
中共建政後第四年,即1953年,開始實施首個「五年計劃」。迄今為止,中國共編製了十四個五年計劃,其中在1963年至1965年間曾因經濟調整而一度中斷。自2006年起,「計劃」一詞正式更名為「規劃」,沿用至今。「五年規劃」勾勒出中國未來五年內的經濟願景、發展目標、重大建設項目以及生產力佈局。
劉銳紹說明,「五年計劃」最初是中國經濟由上而下的部署,屬於計畫經濟體制。然而,由於計劃本身難以靈活應對瞬息萬變的經濟情勢,因此才更名為「規劃」,以賦予其更大的彈性與可調節性。
中國官方將「五年規劃」視為中共治國理政的核心手段。中國國內對此規劃的解讀文章也頻繁引用外國學者觀點,強調中國是為下一代子孫後代而制定規劃,而西方國家則為下一次選舉而規劃,藉此凸顯「五年規劃」的獨特優勢,非西方體制所能比擬。
值得注意的是,「五年規劃」制度帶有濃厚的前蘇聯政治經濟模式色彩。
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許成鋼解釋道,「五年規劃」並非外界常誤解的「產業政策」。它源於前蘇聯模式,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掌控全國經濟的一環,其基礎乃是社會主義制度,亦即「黨領導一切」,所有關鍵且重要的資產皆歸「國有」。
許成鋼教授強調,「黨和國家在設計與執行這項制度時,都是為了服務中國共產黨的長遠戰略目標。」他進一步指出,當規劃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時,這些資金幾乎都來自國有資產。他舉例,目前投入人工智慧領域發展的資金,絕大多數為國有資金。
回顧近年規劃,中國國務院於2015年公布的「中國製造2025」製造產業政策,隨後也被納入「十三五」規劃中。許成鋼教授點出,這並非市場經濟模式,而是要求依照計畫達成預設的數量標準。「中國製造2025」確實讓中國掌控了全球多數產業鏈。然而,他認為,許多分析在評估這項政策成效時,卻忽略了「製造這些產品的真正目的為何」這個核心問題,應該探討其究竟是為了單純的經濟發展,還是旨在提升社會福利保障。
在四中全會召開前夕,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特別召開了經濟形勢專家與企業家座談會,敦請專家學者們「為做好經濟工作和推動『十五五』發展積極建言獻策」。會中,李強重申必須持續努力擴大內需,強化國內大循環,並不斷開創擴大內需的經濟新增長點。
然而,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,消費者物價指數(CPI)與生產者物價指數(PPI)卻持續呈現下跌趨勢。
許成鋼教授分析,這些指數的負成長,明確指出中國正經歷長達兩年多的通貨緊縮,這是一種極為嚴峻的經濟危機。他解釋,當民眾預期物價將持續下跌時,無論是消費者或投資者,都會選擇「持幣觀望」,也就是即使手握現金也盡量避免消費。這種「不消費、不投資」的行為,最終導致「內需不足」,進而惡化通貨緊縮的局面。
他認為,「十五五」規劃很可能將資源集中於技術發展,主要目的是為了與美國競爭。然而,在國家財政赤字與地方債務問題嚴峻的現況下,持續將資金投入科技研發,並無法有效帶動經濟成長。因為中國當前的問題根源在於「需求不足」,而非「供給不足」,且與高端科技技術的發展並無直接關聯。
許成鋼教授表示,中國的投資計畫與戰略佈局雖然成功佔據部分產業鏈,並展現其技術實力,「但實際上這與其自身的經濟發展存在衝突。」他直言:「共產黨統治下的制度,從未真正將內需視為其最終目標。」
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的戴維分析指出,「十五五」規劃的重點,將會放在強調「新質生產力」與製造業,以此作為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。此外,為了應對美國可能對中國實施的技術「卡脖子」問題,透過解決社會不平等來刺激國內消費將是關鍵策略。同時,改善社會治理以維護內部穩定,在經濟持續承壓的局面下,也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戴維教授強調,「五年規劃」並非一份必須嚴格遵循的經濟藍圖,而更像是一份重要的發展指南。預計具體的目標與措施將陸續公布。若規劃內容提及短期內提振經濟的調節措施,這可能暗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將展現出更靈活、更願意進行談判的姿態。
值得注意的是,在中共四中全會結束後不久,亞太經濟合作組織(APEC)峰會預計將在韓國登場。
屆時,美國前總統川普(特朗普)預計將出席峰會。他日前受訪時透露,預計將在兩週內於當地與習近平會晤,並表示100%關稅並非長久之計。